
这是一个热得发烫的夏天,这也是一个山歌响起的夏天。当同样热得发烫的刀郎带着他无坚不摧的音乐利器来到楚辞的源头宜昌,就注定了他与中国诗歌之祖屈原撞个满怀。
是的,在刀郎眼里,屈原一定是他的亲人,是他可以为之倾诉一切的导师,一个可以拥戴、可以拥泣的诗歌之父,是他可以时隔两千多年还能说上话的万神殿上的神祇。而在屈子眼里,刀郎一定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异代知音,一位深谙诗歌三昧的浪漫诠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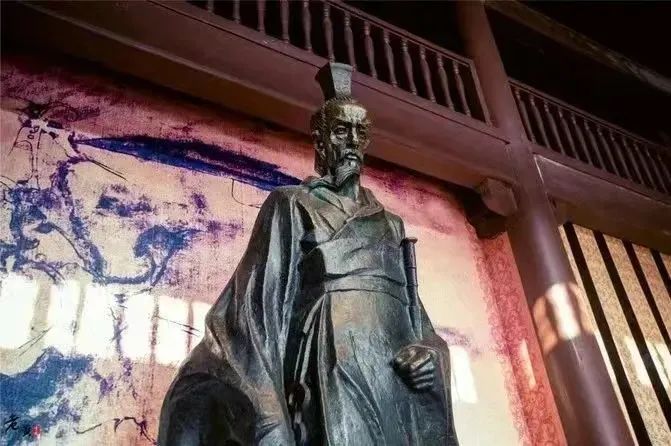
神奇的是,刀郎是带着一只传说中的秭归鸟来到宜昌的。于是,我们分明看到,此鸟非凡鸟,而是一只足以扇动十二级三峡风的神鸟。且看,当刀郎的歌声在《秭归鸟》中撕裂现代音乐的帷幕,我们听见的,不仅是当代歌者的吟唱,更像是一支穿越两千年的“竹枝词”,在江风中呜咽。“弭棹西陵沚,沉歌酹楚魂”,这短短十个字,已然、悄然也决然地将屈原的精魂、秭归的江水、楚辞的韵律统统召唤到我们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一滴不剩。就像屈子通过《离骚》扩展了楚国精神的天空,刀郎在此施展的实则是当代罕见的招魂术,他让一个古老的魂魄在现代歌词中获得了令人颤栗、令人悸动的复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宜昌人心中,通过《秭归鸟》,刀郎已悄然完成了一次身份的蜕变——他不再仅仅是一个歌手,而是一个诗人,一个以音符为韵脚、以屈子为向度、以时代为音符、以思想为底色的现代行吟者。
鸟之于楚人,追溯起来,那是相当莫逆。楚人庄子在《逍遥游》里专门致敬大鸟:“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何其壮阔,何其恢宏;雄才大略的“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借鸟喻己,给我们留下了“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著名典故,何其形象,何其贴切;以楚人自居的李白甚至颇为自得地发声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那睥睨一切的姿态,分明是狂接舆“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在太白居士身上的千年回响,何其深刻,何其平易。而在我们屈子伟大的诗篇中,则更是“鸟去鸟来山色里”:鲁迅集屈子诗联“望崦鹚而勿迫兮,恐鹈鴂之先鸣”,流露的是对时间的挽留,对岁月不居的抗争,这里的鹈鴂,就是刀郎笔下的秭归鸟,她也叫子规、杜鹃、布谷;而《哀郢》中一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同《离骚》中的“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一样,有着浓得化不开的家国情怀。以其衡之于刀郎在《秭归鸟》中一唱三叹的“魂兮归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等关键词,又是何其异曲同工,何其灵犀暗通?
是啊,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一只鸟的鸣叫是多么值得珍视。何况,这还是一只“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的秭归鸟。果然,在刀郎的词中,秭归不惟是一个古老的地名,还是一只古老的鸟,她是一只灵性的鸟,一只高蹈的鸟,一只寻寻觅觅的鸟,一只寻不见哥哥誓不还的坚毅之鸟,这一点,她与“衔微木以填沧海”的精卫鸟又是何其神似。巧合的是,在这里,陶潜的诗文成为连接两只鸟的一条跨越时空的暗线。

图片由AI生成
刀郎有一方心游万仞的思想天空,也有一支飞天入地的神奇之笔,这支笔在通俗、传统和民间三个维度上游走,落纸为墨,下笔成歌,以梦为马,横槊赋诗,这一点,他是深得屈子真传的。在刀郎的词中,月亮控制着时间,青竹象征着君子人格,河流是一个动词,树冠则成为可以驰骋的道路。我还分明感知到他笔下的千载暮雨,不是普通的雨,是王逸注《楚辞》时所说的“巫山暮雨”,是从宋玉《高唐赋》就开始飘洒的文学之雨。而“离骚彻夜鸣”的拟声处理,更让我觉得这一千古名篇,能在暗夜中发出灵动的声响。听,这是何样的声音?我怎么听到骨头拔节的铮铮之声,听到热血涌动的汩汩之声,那里,还有西陵峡口江潮的击浪之姿,还有那位“古老的孩子”昼夜奔跑的身影。你说,这是一只秭归鸟,我说,她也是埋头苦干的人,是拼命硬干的人,是为民请命的人,总之,是一个大写的人。
秭归,显然是这次现象级事件中的赢家。在刀郎的歌词中,秭归被反复书写、反复吟唱、反复咀嚼,秭归鸟一夜走红。而西陵峡口、大江两岸、崖壁灯火——这些意象构成了一幅活色生香的秭归人文地理图景。虽然,屈子诗篇中的兰橘意象在词中完美缺席,但我也分明在字里行间,嗅到了兰之葳蕤之气,闻到了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橘之芬芳。

图丨西陵峡 郑坤/摄

图丨马晓宏/摄
曾几何时,刀郎的神曲《罗刹海市》不胫而走,风靡全世界,让我们体味到音乐强大的统治力和感染力。从另一个角度视之,则是作为音乐人的刀郎,极善于从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灵感,寻找故事之源,然后与古为新,化为原创,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密码。在这一艺术领域,真的,舍刀郎其谁?有之,则要么食古不化,要么不知所云,终是隔山买牛,不着边际。
实际上,在刀郎的歌词里,始终回荡着一种古老的巫性,这一巫性在三峡地区大量存在。从《山歌寥哉》的志怪叙事,到《秭归鸟》的楚辞回响,他的音乐始终在履行一种招魂仪式。“弭棹西陵沚,沉歌酹楚魂。暮雨来千载,离骚彻夜鸣。”这四句诗,几乎可以直接嵌入《楚辞》的某一篇章而不显突兀。刀郎在此使用的不是现代汉语的抒情方式,而是楚地巫觋的咒语式表达。弭棹——停船,酹楚魂——以酒祭魂,这些动作不惟是现实主义的描写,更是仪式化的行为艺术。他的歌唱,本质上是让屈原的魂魄在现代汉语里重新附体,重回诗歌现场。
于是,我们也看到,当刀郎与秭归鸟相遇,出其不意的诗性因子四处迸射,有着挡不住的冲击力。刀郎的诗性,并非来自学院派的修辞训练,而是来自民间未被驯化的语言野性。“一只青竹从我的胸膛里面长出来,枝叶上挂满西陵峡口所有的江潮。”这是歌词,更是民间性十足的诗行,在歌与诗之间,刀郎似乎找到了民间歌谣的密码,这些密码,在刘禹锡为代表的三峡竹枝词里曾经显影,在三峡民间艺人刘德培、孙家香、刘德芳的五句子歌里,通行无阻。在这一点上,刀郎当之无愧可称之为“人民的歌者”,因为他最善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的词,不是飘在空中的抽象抒情,而是扎根于土地、血液和骨骼的文字树。
如果说,屈原的《离骚》之所以不朽,不仅因为它的文学技巧,更因为它建立了一种“诗人—祭司—流亡者”的三位一体身份。那么,刀郎的《秭归鸟》同样如此:他的歌唱,既是对亡灵的召唤,也是对自我流放处境的确认。当他在歌词中反复呼喊“魂兮归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时,他不仅在召唤屈原,也在质问这个时代:当文化记忆日益荒芜,当个人心田日益枯竭,桃花源何在?我们和世界,将归向何处?
“走吧,落叶吹进深谷,歌声却没有归宿”(北岛语),这个世界需要确定性,秭归鸟的声声“我哥回”,就是对确定性的呼唤;“走吧,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这个世界,有枯枝烂叶,有枯竭的心田,有不再浪漫的爱情,有铁一样无法改变的现实,但记忆却不会永远失去,因为总有一片湖水的静谧,让生命唤发生机与活力,化作我们前行的力量。走吧,让我们不断地与刀郎相遇,在诗里,在夜里,在梦里,在每一个值得珍惜的时辰,这正是:“问天问地问人,一卷离骚,写屈子招魂赋;入俗入神入化,千年暮雨,唱刀郎竹枝词。”
我相信,山歌响起的地方,因为刀郎,一定有一只秭归鸟,在我们眼前,飞过!
(2025年8月5日夜)
作者简介:冯汉斌,资深报人,诗人,学者,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日报传媒集团高级编辑、宜昌市作协副主席、宜昌市楹联协会主席、宜昌市屈原学会副会长、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历史遗存学术委员会主任、宜昌市职工文学读书协会副会长等。出版有散文集《归州十八拍》、诗集《与词语对舞》、评论集《以屈原之名》等著作,主编各类专著近十种。





